【 雪山健行 】NEPAL

【 雪山健行 】
N E P A L
前言:
我第一次到 尼泊爾 ( Nepal ) 高山地區健行是我30歲那年。
8年後,我又去了一次 尼泊爾 的Simikot 當義工。
那次性質雖然不能歸類為旅遊,但我在 Humla 前前後後走的山路倒也不少。
Simikot 的生活經驗,我已經將它記錄在《雪山上的醫院》那篇文章裡。
所以說,這一篇《雪山健行》的年代是有些久遠呢。
時間點之所以有前後互調的紊亂,就怪罪COVID疫情吧。
去年我才回到紐西蘭的家,這才有機會將尼泊爾的照片翻出來。
如此一來,我到尼泊爾的首次健行,只好將它以札記的型式在此發表了。

16歲的小挑伕憂心的望著我,他肩上扛著的是我的大背包。
我們緩緩走下山,四周雪白一片,山坳裡不時傳來轟隆隆的雪崩聲響。
我們[這一團]一共6個人,全來自馬來西亞的登山社。
2個月之前,我才剛和在高中教書的盧老師 Lu ,以及他的幾位學生一起去爬完[大漢山](Gunung Tahan)。
或許 Lu 覺得我的體力還好,能和他們 5個男生一起上 喜馬拉雅山 去健行?
也或許他們就是 6 缺 1,而我是莫名奇妙被抓去湊數 ?

抵達 加德滿都( Kathmandu ),我們被帶到一個尼泊爾人的家中去做客。
主人烹煮了一桌當地的美食請我們,大夥兒也吃得不亦樂乎。
但是有一件事情,至今仍讓我百思不解。
我記得上飛機之前,Peter讓每個人在免稅店各買一瓶洋酒,說是幫那個尼泊爾主人帶貨。
Peter還說,那個主人之後會將那瓶洋酒的錢還給我們。
在那個年代啊,一瓶洋酒蠻昂貴的。
我當時傻乎乎,人家邀,我就走。從不知害怕,看不見危險,我更是不知別人袖子裡耍什麼套路。
果當然爾的結果:那餐 尼泊爾美食 真是很昂貴,值一瓶洋酒的代價。

直到有一天,我方才知曉我們每日氣喘噓噓在爬的山路叫:
安納布爾納環線 ( Annapurna Circuit )
因為那天傍晚我正在研究地圖,卻越看越糊塗,就問那5個男生:
「你們看,這下面有一條公路。如果要從A前往B,咱們為什麼不坐巴士?」
他們像似聽到世界上最有趣的笑話,一個個笑到流淚,一室笑聲嘩然。
「我們就是喜歡走路啊,Jane !」
原來我是那個唯一不知道自己在幹嘛的大傻瓜,我也懷疑當年自己的腦袋裡是否都裝了漿糊。


6個人當中,只有剛從英國留學歸來的 Peter 有過雪地經驗。
所以某個黃昏,當我們在Manang的山坡練習穿冰爪、使用冰斧時,我突然意識到這整個行程有多荒謬。

我們雇用1個嚮導和4個挑伕。
Peter 的計畫是健行走完14日的Annapurna 環線,中途去攀爬 6419公尺的 Chulu 西峰。

那天我們上到 5100 公尺的基地營時,我的兩鬢開始劇烈疼痛。
於是我吞下2顆止痛藥,躲在營帳裡躺平3個鐘頭。
當 painkiller 證明無效時,我知道自己得了高山症。

無奈,我只能往下走到低海拔處。
2天後,將近天黑之際,只見5個大男生病懨懨、沉默的從山上走下來。
他們沒有登頂是意料之中,但是5個人之中有3個劇烈的在咳嗽,還咳個不停。
聽説他們得的是[水肺]。

雖然6個山友當中有3個人在生病,我們卻只在Manang 附近的民宿留住一晚。
隔天我們繼續趕路。
因為再來的Thorong La隘口海拔是5416 公尺,對每個人都將是大挑戰。
維基Wikipedia上有記載,2014年10月的雪災造成了43人死亡、50人失蹤。
那次暴風雪加上雪崩,造成尼泊爾健行歷史上最嚴重的災難。
通過隘口的前一晚,4個男生在房間睡覺,只有Peter陪我在小旅館的餐廳喝青稞酒。
記得Peter好像是先在英國留學,之後他才從紐西蘭的大學拿到學位。
也或許我搞錯了,但是那些都不重要。
我只記得隔日我們往上爬隘口的那個艱難路段,Peter一路都陪伴我照顧我。
他還脫下他的藍絨大衣讓我穿。
如今想想,若是當時Peter沒有給我那件溫暖的外套,加上不斷鼓勵與照料,我要跨過那5416 公尺高的 「坎」 ,或許有極高的難度。

在經歷高海拔的山區健行訓練之後,下山路段簡直可以用「健步如飛」來形容。
路上我曾經遇見過一個香港人,他甚至穿著夾腳拖,一路蹣跚走到山底。
香港人和我無所不談,相處蠻融洽。
之後,我遇見一位我在Manang認識的法國隊嚮導Mudi,他邀請我去他家吃晚餐。
在獲得Peter的同意之後,我終於正式脫隊、告別那5個大男生。

Mudi是尼泊爾人,他介紹我認識他們的團隊,有嚮導也有porters。
我們後來一起去看著名的魚尾峰(Fishtail Mountain)日出。
到了加德滿都,我們用手吃Thali,Mudi還帶我去當地人最愛的戲院看電影。
山下是不同的世界。
但是我已經迷上尼泊爾文化,這也種下8年後我重返Nepal的因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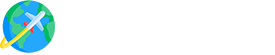


一般留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