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我愛上一株水仙】 Echo ξ Narcissus

【我愛上一株水仙】
Echo ξ Narcissus
作者: 陳慧娟
前言:
感謝當年《海外迴響》的編輯,so kind,竟然允許我將近4000字的篇幅,
能在副刊專欄裡滔滔述說那一段蒼白的邂逅與情感掙扎。

想著他漸行漸遠,哀傷、憂鬱就像甜美的毒藥般,一滴滴地滲入我的神經,浸滿我的心靈。
何時才能自這幸福又痛苦的幻覺中醒來?
我不曾想要過他,也不曾想過我有機會擁有他,我們之間只有短短的5天。
而這5天就像流星在天空相遇的際會,短暫,但美麗。
沒看過像他長得這樣「美」的男子。
那憂鬱的大眼睛,那雕像般的輪廓,還有那剪得短而合時宜的栗色頭髮……
無處不美。
而他也像「水仙花故事」中的少年,一樣地愛著自己。
或許這輩子得到的讚美太多了,多得有如繁星,因而他顯得蒼白而敏感。
他纖細的情感,隨時都會像迅速凋萎的花朵那樣,跌入低潮。
然而,這樣的男子卻是被眾女子所寵愛的。
他是朋友丈夫的同窗好友,來自美國芝加哥,曾在銀行裡工作過。
今年,他毅然辭去了工作,揹著大背包,打算徒步走遍東南亞。
在他未來之前,有一天,朋友指著他的相片說:「弗烈德就要來馬來西亞了。」
照片中的他,姣好、帥氣,而且充滿了自信。
他一飛抵新加坡,便受到各方熱烈的招待。
女子們爭相打電話查詢他的行蹤,請他上館子,還細心地替他安排行程。
朋友的丈夫M也是美國人,我們兩家約好帶弗烈德到國家公園玩。
國家公園在彭亨州,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叢林。
從吉隆坡出發,約兩小時的路程始可抵達淡美令渡口。
由淡美令渡口到國家公園的心臟地帶,必須搭乘長船。
長船只容納10人,一路破水前進。
兩岸是茂密的叢林,群山在眼前向我們伸出熱情、歡迎的兩臂。
弗烈德坐在我的左前方,不時回過頭來對我們說話或開玩笑。
正午時分了,陽光愈加強烈。
於是我戴起了墨鏡,弗烈德也跟著拿起胸前的墨鏡戴上。
河兩岸時有藍羽水鳥飛上飛下,有紅葉、黃葉飄旋落在水波上。
是故船程的後半段,我們都靜靜地欣賞眼前的美景。
約近國家公園時,晴空裡閃現一片烏雲。
接著,雨點斜斜地打進船艙裡來。
眾人忙著遮掩,弗烈德和我卻高興得拍手歡呼大叫。
那種豁出去的快樂是無法形容的。
弗烈德這個人醉心於美好的一切。
因而,他也無法忍受一絲絲的缺陷。
他喜歡美好的事物,或是聽到美好的話語。
為此,他可以像小孩那樣的開心快樂。
否則他寧可抿緊那線條美好的雙唇,讓自己陷入莫名的憂鬱裡。
大部分的時候,他喜歡別人注意他,因為他知道自己長得好看。
在別人的眼光中,他尋找到自信。
他是一篇意境美、文詞漂亮的詩,但卻不帶特定的內涵或意義。
而我,一顆寂寞的心正在尋找愛情。
多年的婚姻,已使我忘記戀愛那醇酒般、醉人的滋味。
如今,我疲倦地將自己的心開放成一座不設防的城。
5天,啊,在這短暫的5個日夜裡,且讓我再嘗那愛的蜜汁吧!
抵岸的第二天,他和一夥人便乘船去釣魚。
午後回來時,趴在床上休息。
我剛洗過澡,頭髮溼漉漉地垂了一肩,身上穿著一件艷紅色的T侐。
一日不見,他乍見我時,欣賞的眼光中透露著驚喜。
爾後,他回過神來,愉快地向我說:「嗨!」
我笑問他垂釣的結果。
他興奮地說他們今天在水邊泥地看到老虎的腳印,不過竟日裡只釣著兩尾小魚。
我們笑著、聊著,而我知道,這個蒼白、敏感的年輕人已經開始喜歡上我了。
他平時不主動去和別人攀談,而往後數日卻常藉故來找我說話。
丈夫用著懷疑的眼光看著我們。
過去,他是一個粗心、毫無情調的男人。
如今,他卻亦步亦趨地跟在我身邊,用著嫉妒的語氣,尖酸刻薄地挖苦弗烈德。
我知道,他若有機會,一定會將弗烈德推落十八層地獄。
朋友在第三天的早晨便先回吉隆坡去了。
我獨自在餐廳裡喝著咖啡。
潔白的抽紗餐巾,香味醇厚的咖啡,還有草地上、林間裡飛躍的鳥兒……
這一切都讓我的心情清新而且愉快。
這時,弗烈德在晨曦中自長廊那端走來。
我向他招手。
「早!」,他愉快地坐在我對面,替自己叫了一壺紅茶。
我們天南地北地談起文學,以及在世界各地旅行時的見聞。
他滔滔不絕地說著話,還不時偏著頭笑。
那漂亮的臉、那一口潔白的牙齒,使得他的笑容更加純真、動人。
丈夫幾次來催,朋友也來告辭過,我們卻像視而不見。
當天下午,眾人打點好背包,出發走向叢林。
那日晚上,我們預定棲息在觀察動物的高架木屋裡。
黃昏時,木屋裡新來了一位叫戴倫的澳洲男子。
戴倫和我坐在台階上說話,丈夫、弗烈德,以及M則在一邊炊事。
戴倫正高興地談他在巴厘島參加的一場婚禮。
弗烈德則皺著眉頭,倚著樹幹看我們。
他時而不安地走動,又生氣地走回樹幹旁。
看得出,戴倫在他眼中是一名入侵者。
戴倫,一名來自澳洲墨爾本的小學老師。
他人很和氣,肯吃苦,來東南亞後便儘量適應熱帶的氣候和食物。
而弗烈德卻正好相反,他是嬌生慣養的。
他挑食,埋怨木屋裡奔跑來去的老鼠,連夜間飛行的蝙蝠都會惹惱他。
叢林的夜是靜謐的。
我因為頭疼,早早入睡,作了許多惡夢。
驚醒時,弗烈德正在叫我的名。
「Jane,妳醒了嗎?」
「嗯,什麼事?」
「我睡不著,這床上有一隻老鼠。」
這個男人怕老鼠呢,我在黑暗中偷笑。
我爬下床來,和他躡手躡足地走向窗口。
然後我們持著強電力的手電筒往叢林間照射。
「瞧!那裡有一隻鹿。」弗烈德很高興地指著黑暗中一對晶亮的眼睛說。
「嗯,這邊還有一隻!」
諾大的木屋裡只有我們兩個清醒的人,彼此感到特別的親密。
翌晨,我早早起床,揹起長鏡頭相機,向潤溼、陰涼的叢林走去。
我一邊享受林間的清靜,一邊獵取各種叢林風貌。
回到木屋時,弗烈德坐在台階上,看來才醒不久。
今晨,我換過一套黑色鑲鑽的T侐及牛仔褲。
從他的眼光中,我再度看到那閃現著的、欣賞的光芒。
他是很注重穿著的男孩,經常擔心衣服搭配的問題。
由於旅行期間不能帶太多的衣服,所以他常為此煩惱。
其實什麼衣服穿在他那勻稱、健壯的身上都是瀟洒不羈的。
他的一舉手、一投足都是美。他還苛求什麼?
坐了一會兒,他突然說:「Jane,可以陪我去爬Teresek Hill嗎?」
我瞪著他看,似笑似謔地說:「真的?你確定要去?」
因為我明白他並不是愛爬山的那種人,而且昨日我已爬過Teresek Hill,知道那座小山有幾乎成九十度的斜坡,這小山準會教他大吃苦頭。
但是,我有點惡作劇地應允了他。
澳洲人戴倫說他也想跟去。
我們三人循廢棄的叢林小徑前進。
我走在最前頭,然後是弗烈德,再來就是戴倫。
我輕鬆地越過橫在小徑上的腐木,攀藤直上。
不多時,戴倫就大聲喊停。
他說:「Jane,妳這不算hiking,簡直是在跑嘛!」
於是,我讓戴倫走在前頭,弗烈德殿後。
弗烈德此刻已汗如雨下,臉色更加蒼白,我真擔心他隨時會昏過去。
這時,晨曦自林間篩下,美極了。
我們花20分鐘的時間便抵達山頂尖。
四野是一望無盡的山巒起伏,連半島最高峰 – 大漢山,也隱隱約約在雲霧的那端。
戴倫在回程中轉去河邊游泳,我和弗烈德則慢慢走回木屋。
整個叢林裡就只有他和我。
我們話說得不多,只用眼睛和笑容來交換彼此內心裡的感覺。
在這樣一個美好的清晨,能和這樣美好的人在林中漫步,我整個心靈、整個人如沐浴在無可言喻的幸福之中。
丈夫在我們抵達木屋時,以憤恨怨怒的眼光盯著我們看。
自此,只要有弗烈德出現的場合,他都會強拉我到別的地方,或是故意說些夫妻間親密的往事給弗烈德聽。
弗烈德聽後總皺著眉,緊閉著嘴唇。
前一分鐘他還興高采烈地替我洗飯盒,後一分鐘聽丈夫說今晚要和我睡帳篷,他便生氣地跑開了,一個人躺在河邊的長椅上,蜷曲著。
明天就要回吉隆坡了,就要回到塵世中的一切。
Party is over,他哀傷地望著夜空,知道離別近了。
那才剛要綻放的、愛情的花朵就這樣地凋零枯萎了。
他恨,委實恨。
但是,又奈何?
我望著他的背影,全身像得了重病似的痛苦萬分。
靜靜地躺在帳篷外的草地上,一絲一絲的憂鬱漸漸的籠罩我……
方知,離別所帶來的感傷竟是如此巨大。
翌日,回程的船上,弗烈德堅決不和我們夫婦同船。
他冷漠著一張臉,好像全世界都得罪了他。
我讀著三島由紀夫的《愛的飢渴》。
唸到那一段「……像登山家追求險阻的山峰一樣,悅子被不安與痛苦所慫恿,造成了更多的不安與痛苦。」,霎時覺得生不如死。
Party is over,他知道,我知道,我不怪他。
在叢林的那72小時,我們已盡力扮演了自己的角色,也拿出了一顆真心去維護一切的美和善。
我很滿足,我不苛求永遠。
而他是一個纖細的人,他的感情觸角太過敏銳。
這原是一場「禁忌的遊戲」,我們不可能持續下去。
持續下去,惟有破壞我們一路來建立起的美感。
而當那時,愛將不再美麗,我幸福的夢亦將破碎。
年歲的經驗告訴我,那種破碎的痛苦必比現時「快刀斬亂麻」的決定來得更痛苦。
而且我也相信;那樣的幸福只可能發生在那樣的空間、那刻時間裡。
過了,就沒有了。
刻意的延續,一樣是失去美感的命運。
再會了!
一路上望著他出色的側影,使我想起自己在中學時看過的一部電影《癡情佳人》。
那是一個伯爵夫人愛上詩人拜倫的故事。
她追求他,甚至當著他的面割腕自殺。
但是拜倫已不再愛她,伯爵夫人終於心碎而死。
電影映畢時,我哭得淚溼滿襟。
成長的過程中,我常懷疑自己當時為何會為那段「出軌愛情」如此地感動。
或許,我的內心裡早已經埋伏下同樣的悲劇種籽吧。
弗烈德不是拜倫,他只是Narcissus,一個愛上水中自我的美少年。
而我,謹記要自己別憔悴成癡心的Echo。
然而又為何,睜眼閉眼,總是他的臉龐浮現?
原文 刊載於 台灣日報《海外迴響》專欄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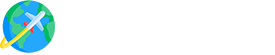


一般留言